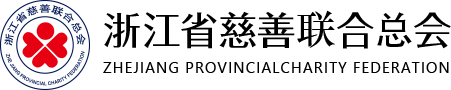浙江工商大学英贤慈善学院特聘教授叶正猛在《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6卷第6期发表论文,论述“士”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价值的守护者和发扬者,在中国古代慈善事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古代慈善事业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形成了鲜明的特色。传统慈善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士”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价值的守护者和发扬者,在中国古代慈善事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 、“士”的本质:作为精神价值的守护者和发扬者
中国“士”的传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独特现象。钱穆认为:“中国文化有与并世其他民族其他社会绝对相异之一点,即为中国社会有士之一流品,而其他社会无之。”[1] 余英时则认为:“如果从孔子算起,中国‘士’的传统至少已延续了两千五百年,而且流风余韵至今未绝。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2]
什么是士?学界对其的具体表述、看法不尽相同。根据赵剑敏的定义,中国古代的“士”是个“带有文化含义的广泛复合体”[3]。何立明指出:“在古代中国,士人首先是一个社会阶层,位于‘士农工商’四民社会最上端。其次,士人是一种存在类型,‘耕读传家、诗书济世’是文化特征。第三,士人是一个精神群体,是‘把品性作为生命’的一群人,是道义、气节、趣味、礼仪的源泉。”[4]易言之,作为精神群体的“士”并非指向某一个明确的阶级,并非以集团的形式存在,而是分散在社会各个层面,只要符合学识、精神层面标准的,就是“士”,既可以“居庙堂之高”,也可以“处江湖之远”。
士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价值的守护者和发扬者,其社会角色意识“主要表现为对一种自觉的精神与人格榜样力量的自我认同。……这与‘现代性’以来围绕社会生产分工而派生的职业角色意识有质的不同。在传统社会里,他们实际所承担的是一种‘道德分工’。”[5]“以天下为己任”构成了士的精神价值底色,余英时指出:“孔子所最先揭示的‘士志于道’便已规定了‘士’是基本价值的维护者;曾参发挥师教,说得更为明白:‘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一原始教义对后世的‘士’发生了深远的影响。”[2]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论及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时,列举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等[6],其间所提及的范仲淹、陆游、林则徐、孟子、文天祥、诸葛亮等古代人物,均是精神意义上的“士”,反映出“士”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中国古代慈善事业是“士”发扬“以天下为己任”这一精神价值底色的重要场域。明代王畿认为:“一乡之善士以一乡为家,一国之善士以一国为家,天下之善士以天下为家。其心愈公,则其善愈大。其所为善,乃心与人同,视之如一体,是所谓公也。”[7]“济弱扶倾,方为杰士。”[8]士孜孜不倦地向社会流布“仁爱”这一善的理想,并积极投身于古代中国慈善事业,既运用自己的财产和人望积极从事民间慈善,又兢兢业业做好政府慈善工作,成为中国古代慈善事业的主要角色,在中国古代慈善事业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二、样本画像:中国古代慈善事业中的士人群体 “士”在中国古代慈善事业中到底占据何种重要地位,笔者尚缺乏足够的统计数据对其进行全面的量化分析,但可以通过如下两个不完全的统计样本大略一窥其貌。 一是“慈善人物中的士”样本。位于江苏南通市的中华慈善博物馆设有“仁为己任,积善成德——慈善人物展厅(古代)”,展示了从春秋时期‘首善’范蠡到近代创造南通‘近代第一城’美誉的张謇先生,不同时期、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慈善代表人物。展板展出和屏幕显示的中国古代慈善人物共 68 位。经查考,其中可以归为“士”的四十多位,占近 70%。例如,宣秉,东汉冯翊云阳(今陕西大荔县)人,把历年所得的俸禄,常常用来收养亲族。对于那些孤寡贫弱的族人,则分给田地,自己家却无一石粮储存,常服布被,吃蔬食,用瓦器。李邕,唐朝鄂州江夏(今湖北鄂州)人,唐代大书法家,好尚义气,常用家资来拯孤恤穷,救乏赈惠,积而便散,家无私聚。吴师道,元代婺州兰溪县(今浙江兰溪)人,任宁国路录事时,大旱,饥民载道。为广济饥民,让其存活,吴师道劝谕富家巨室,筹集粟 37 600 石,并向朝廷奏准,拨赈粟 4万石,钞 38 400 锭,三十余万人赖以存活。袁黄,明代浙江嘉善人。曾任明代宝坻知县。编著《了凡四训》,借助因果报应观念,建立修身立命之说,并推广积善改过的劝善实践。蔡琏,明末清初江苏宿迁人,于崇祯七年(1634)在扬州创办育婴社,邀集同志,以四人共养一弃婴,每人每月出银一钱五分。此为明末第一个以育婴为目的而结成的善会。清初,蔡琏又建立扬州育婴堂,并主持其事,至康熙十六年(1677),养活幼婴三四千人。值得关注的是,列入慈善人物中还有几位僧人,有的是由士人皈依的;另外还有几位名将,如钱穆所言,“中国文化传统上有一特殊之点,即对文武观念向不作严格区分。历史上名将大帅,极多数是文人学士,儒雅风流”[1]2,似也可纳入“士”的范畴。如按此统算,慈善人物中的士比例会更高。虽然中华慈善博物馆对慈善人士的遴选标准不是绝对的,但对于管窥慈善人士的身份构成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与之相印证的是,《中国慈善简史》叙述历代个人行善的,记叙最多的是士大夫这一阶层的“仁者善士”。其中,宋代范仲淹、苏东坡、真德秀,明代吕坤,清代唐甄,等等,都是一代儒士。 二是“绅士中的慈善人物”样本。张仲礼的《中国绅士的收入》一书附录了作为研究对象选取的全国各地“地方志人物传”摘要。经研究,发现其中明确有行善纪录的占绝大多数。附录一“出仕的绅士”选入 82 人,其中有慈善纪录的 67 人,占比达 81.71%;附录二“从绅士功能获得收入的绅士”选入 165 人,有慈善纪录的达 154 人,占比达 93.33;附录三“充当幕僚的绅士(为绅士中收入较低者)”选入 78 人,有慈善纪录的 15 人,占比为 19.23%;附录四“从教学获得收入的绅士”选入 173 人,有慈善纪录的 84 人,占比为 48.55%;附录五“绅士地主”选入 88 人,有慈善纪录的 69 人,占比达 78.41%;附录六“从商务活动获得收入的绅士”,选入 42 人,有慈善记录的 31 人,占比达 73.81%。[9]张仲礼的研究本不是针对慈善,因而所选取的样本对于慈善研究而言更具有随机性,也更有可信度。例如,甘泉的符燮梅,是位贡生,在江苏的很多地方做过学官。他力行善举,为一些慈善机构详定章程。1860 年发生洪灾时,他参与筹赈、勘工等,事无不举。山东历城的李春元,光绪时进士,府学教授。家贫,两个弟弟出外经商。他曾主持过书院,并认真研究家乡河道的走向,以及河流改道后所坏田庐的状况,俱绘制成图,并筹划兴工修缮所需的劳力和经费来源,当地的居民都因此从中获益。嘉兴沈学诗,嘉庆时贡生。其主持了一个施粥的粥厂,并兴建浮桥,修筑引水渠道,以广灌溉。此外,如恤嫠、助葬诸义举,基无不踊跃从事。南海的伍崇曜,道光时特科举人。系行商,其连同其父亲,先后捐助不下 1 000 万两银子,为海内之冠;还与新会的卢文锦共捐资 10 万两银子修建石堤,并为广东大吏借到了 26 万余两银子的外国贷款。 这个样本与周秋光等著《中国慈善简史》所言的“我们在方志、杂录中也能查到‘岁费千余金,皆士大夫助之’之类的记载”[10],是相一致的。该书多处记载,明清时期民间慈善多有“绅衿”主持,“对社会福祉事业十分热忱的地方绅衿及其他有力者的捐输”[10]2,促成了各类民间慈善组织的振兴。有情怀有品位的地方绅衿、士绅便是民间之“士”。史学家许倬云的记述也可作为印证:“记得在我年轻的时候,在我们家乡,这批士绅基本上管了所有的地方社会福利,所有的救苦济贫、养老扶幼,孤儿院、寡妇堂、无家可归人的收容所,都是这些人在经营……一群受过教育的地方精英,他们不一定很有钱,因为他们品行不错、对人好,他们变成地方性的领袖,大家尊敬的所谓士绅,士绅并不一定有官位。”[11] 如上两份样本,既证明古代慈善人物中,士占绝大多数;也证明士绅阶层中,慈善人物占绝大多数。应当说明的是,上述“绅士”“士大夫”每个个体不一定都属于“有道之士”,但“士之秀者”就在其中。从一个断面可见,士这个群体是古代行善的主要力量。 士,特别是“在职”的士,之所以成为古代慈善捐赠的主要力量,除了情怀之外,客观上是因为在工商业不发达的古代,士人属于收入较高的群体,客观上具备参与慈善的经济条件。白居易有诗:“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俸随日计钱盈贯,禄逐年支粟满囷。”[12]可见其收入确实不低。《显微镜下的古人生活》一书指出:“在古代,官员是高收入阶层。”“读书人就是当不了官,一直做教书先生,工资也相当可观。”[13]地方官员除了俸禄之外,还有其它合规收入。前引《中国绅士的收入》附录一至六中各类型绅士参与慈善的比例也显示,收入较高的绅士,参与慈善事业的比例越高。 三、慈善思想:“士”参与中国古代慈善事业的理论基础 中国慈善文化源远流长,慈善思想相当丰富。牟钟鉴认为:“两千年中华思想文化在动态中形成的结构可用‘一二三多’来概括。‘一’是儒家主导,‘二’是儒道互补,‘三’是儒道佛合流,‘多’是包纳其他宗教和外来文化。这个结构模式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与开放性的有机统一。”[14]“三教虽殊,劝善义一。”[14]2 古代儒道佛的慈善思想都为慈善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但儒家慈善思想在其中占主导地位,发挥主要的引领作用。在孔子仁爱思想奠定儒家慈善思想基石之后,历代士人学习、继承、弘扬慈善思想,并以自己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加以拓展丰富,形成了儒家慈善理论丰富的脉络,学界多有论述。以下简述古代慈善“实干家”中的慈善创新理念加以补充说明。 其一,“博施济众”的慈善境界。《论语·雍也》:“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从儒家仁爱的“差序格局”来看,子贡对“博施济众”这一慈善境界的追求十分超前。十九世纪爱尔兰历史学家威廉·莱基提出“道德圈”理论,认为人类道德圈一开始很小,后来随时间的推移不断扩张:最初,仁慈善心曾经只限于家人,后来圈子逐渐扩张,首先扩张到一个阶级,然后扩张到一个国家,再后来扩张到国家联盟,之后扩张到全人类[15]。以此为标准,子贡的“博施济众”理念已经“破圈”,达到了最高境界,这是子贡对中国慈善理念发展不应忽视的贡献。 其二,“回报世人”的慈善观念。对于中国古代慈善精神,西方学者错误地认为,慈善“这种精神是中国人完全缺乏的”[16]。如阿瑟·史密斯认为,“中国的确不乏慈善之举,从政府到个人。但仔细观察,也许会发现,中国人行善都是有实用目的的,行善是为了积德,积德是为了有个好报应”[17]。中国古代士人从事慈善事业具有强烈的入世色彩,固然无法完全排除“报应”“积福”等具有宗教色彩的因果论的影响,但更多的是因为古代士人强烈的“回报世人”的态度。明末清初慈善家陈龙正提出,积富回报只是给世人带来更大的“善”,“行一善,共悦之。救一人,共感之。万口一气,万心一气,是为大通”[18]。他主张,只有不考虑个人利益的善行才是真善;只有当人既不指望来自上天或人间的回报,又没有计划把自己的功德传给子孙时,善才是彻底的。与陈龙正同时的慈善家高攀龙也有相似的观念[18]2。陈龙正的“回报世人”观念是难能可贵的,是对阿瑟·史密斯论调的有力反击。 其三,“慈善信托”的慈善思维。慈善信托是现代化的慈善思维,指把一部分财富分割出来,用信托的方式世代管理这部分财富,从而实现施惠他人的目的。实际上慈善信托理念其实早就深植于中国历史传统,最早系由范仲淹萌发。范仲淹开创性地置田办义庄,专门挑选本族内孝贤子弟作为这种慈善事业的受托人,参与管理,制订了《义庄规矩》。有人有规,有章有法,成了中国历史上慈善信托的标志性事件。研究范氏义庄的汉学家将其定义为“一个以宗族名义持有的信托财产”[19]。范仲淹虽然没有直接提“慈善信托”的字样,但其制订的 13 条义庄规矩就是一个慈善信托的文本,并对后世慈善的组织形式产生重大影响。 其四,“自立谋生”的慈善理念。资中筠说,中国传统慈善对残疾人的救助主要是出于怜悯之心,“鳏寡孤独废弃者皆有所养”,重在“养”。但到清朝晚期,慈善理念的现代化已经初现端倪,其中代表性人物是张謇。最初在中国兴办残疾人教育使其有自立本领的是外国传教士。张謇明确提出此事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办,其所创办的南通狼山盲哑学校在当时为数不多的聋哑学校中影响最大。张謇也最早提倡尊重残疾人与常人一样的人格,明确办校宗旨为:“造就盲哑具有普通之学识,必能自立谋生”,“以三四年教育犹可使成材,供社会之需而自食其力”。资中筠指出,张謇的一大功绩是“引进了对残疾人积极救助的现代观念”[20]。张謇主张“授人以渔”,让受助人“自立谋生”,呈现出了士人现代先进的慈善公益观。 四、作为主导者:“士”与古代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 吕洪业认为,古代慈善历经上千年发展,薪火相传,呈现出稳定的传承性[21]。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古代慈善可分为民间慈善与官办慈善两类。士在中国古代民间慈善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中国民间慈善发展有一些重要节点,士多能发挥了开创和引领作用,其突出者例举如下。 吕洪业认为,中国早期慈善萌芽于西周时期,并获得初步发展[21]2。一般认为,春秋时期范蠡是中国首善。如果细究,中国民间慈善首善并非仅仅一人,还有一位是范蠡同时期的孔门高足子贡。《盐铁论》明确记载了子贡行慈善的事实:“子贡以著积显于诸侯,陶朱公以货殖尊于当世。富者交焉,贫者赡焉。故上自人君,下及布衣士,莫不戴其德。”[22]这条记载足以证明,在孔子儒家思想的熏陶浸染下,子贡形成了富而好礼的品质,从事民间慈善了。另有“子贡赎人”的典故见于《吕氏春秋》:“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来而辞不取其金。”[23]“子贡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资助乃师讲学授徒,为其周游列国创造条件,‘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也有益于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24] 子贡可谓最早从事慈善的士,在中国民间慈善发展早期发挥了率先垂范作用[25]。 “宋朝是中国慈善事业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10]3 在宋朝,士人参与慈善事业成为潮流,其参与慈善事业比以往的每个朝代都更为熟练,有着特殊的形式,有自己的组织。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范仲淹,其“平生好施与,择其亲而贫,疏而贤者,咸施之”[26] ,做了大量慈善捐助,其中最有意义的慈善之举是于北宋皇祐元年(1049)创办了苏州范氏义庄。这是中国史料记载的第一个非宗教性民间慈善组织。标志着中国古代民间慈善事业的组织化。范氏义庄创造了一个奇迹:其历经战乱动荡、朝代更迭,却一直运行良好,直到清朝的宣统年间,范氏义庄依然有良田 5300 余亩,慈善事业持续运行了八百多年。 明末清初,在大批士人的推动下,中国出现了最接近现代意义的民间慈善事业。宫蒲光指出:“特别是明末清初,江南同善会盛极一时,京城及各省纷纷效仿。社团慈善作为民间慈善的主要形式之一,是中国历史上一种全新的、非官方、非宗教、非宗族的慈善救济形态,是古代慈善事业组织化、大众化、民间化的萌芽。”[27]晚明清初,众多超越家庭、阶级和宗教界限的慈善团体纷纷建立,并实现了跨区域的慈善组织的建构,慈善热潮席卷了地方社会。同善会(筹募善款和其他救助)、会馆(救济同乡)、清节堂(救助贞女孀妇)、骼会(救助贫民丧葬)、族田义庄(救助族人),这些都是当时民间慈善组织发展的硕果。至此,中国古代慈善组织的完善程度达到了最高点。 “士”在晚明清初慈善的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慈善团体主要由士人所主导,“士绅,既是慈善事业的‘主心骨’,又是维持慈善事业的‘润滑剂’”[28]。杨东明、高攀龙、陈龙正、陆世仪和祁彪佳正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这些在不同层级的科举考试中显露头角的读书人,身居庙堂之上则为帝国官僚系统中的士大夫,克尽为官之责;而后退处江湖之远则为地方士绅,于地方事务中尽一己之责。居官而能福其民,居乡而能福其乡。由他们主导慈善事业,展示了独特的优势,既有着中国特色的儒家理念的支撑,同时还在政府与地方之间、在公领域与私领域之间维持着有机的互动。他们对于慈善事业的不同介入,使晚明慈善事业呈现出别样景象。 迄至晚清,中国出现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公益事业。资中筠曾明确指出,认为中国的公益起步只有二三十年的时间是走进了认识上的误区,“公益事业——这里特指现代公益模式,而不是古已有之的扶贫济困的观念——在中国也非始自今日,而是百年前就已开始。”[20]2以商为业的士人是晚清公益事业重要推动力量,其中代表性人物为张謇。慈善家张謇建立起以师范教育为主,包括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以及技校、职工学校等在内的多层次的教育机构体系。 改良或革新育婴堂、养济院、栖流所等传统善堂善会,创兴盲哑学校、残废院、贫民工场、博物苑等近代新型的慈善公益机构,在南通构筑了一个具有近代色彩的慈善公益组织体系。“张謇是最早的新型企业家兼慈善家。……可以说以张謇为代表的实业家从理念到实践都符合现代的企业社会责任,而且理想更高远”[20]3。“言商仍向儒”,张謇是带着士的抱负、士的情怀进入商界,高瞻远瞩追求社会福祉。 五、作为推动者:“士”与古代官办慈善的发展 士人除在古代民办慈善中发挥主导作用之外,也有力地推动了古代官办慈善的发展。周秋光指出:“回溯中国历史,又有官办(政府)慈善一说,且在传统慈善事业格局中占据主导位置,并存续至今。”[29]古代官办慈善主要由地方官员执掌、推动,士大夫作为地方官员的主体,在慈善事业中占据重要地位,有力地推动官方慈善的发展。 古代官办慈善历史有一个大悖论。一方面,封建专制制度是产生贪官的温床。贪官污吏一直在侵蚀、玷污着慈善。“检视众多的灾荒及赈济史料,一些利欲熏心的墨吏污官乘散赈之机大肆克扣侵吞,‘假公委以济私情,冒官物以充己橐。’”[10]4 邓拓的《中国救荒史》也记载大量地方官员“舞弊”“贪污”“剥民”现象[30]。另一方面,追求精神境界、向往理想人格的优秀文化传统,又造就了绵延不断的优秀之“士”。“儒家思想支撑了士大夫道义精神的显现和发扬”[31],“与天地合其德,与四时合其序”[32],出淤泥而不染,挣脱私欲藩篱,承担社会责任,慈善事业大有作为。透过这个“悖论”,逾见有识之“士”难能可贵。贪官污吏是政府慈善的破坏者,康熙甚至认为天灾是“大臣不法,小臣不廉”招致的[33];而“士”才是正能量,就其角色作用而言,士人是官办慈善的落实者、推行者、创新者。 一是士人作为官办慈善的落实者,积极落实中央政府的救灾、慈善的部署。地方官员行事态度决定了落实的成效。《中国慈善简史》指出,“我们从有关资料中找到(元代)地方官员‘认真执行’慈善诏令的例子”[10]4。如福建邵开路同知郭瑛置惠老慈济堂以居穷民无告者,买田若干顷有为堂产,收取地盘以供养入堂老人。东汉苏章、元代吴师道等等,也是落实工作做得好的代表。苏章任武原县令时,恰逢荒年,他开仓放粮赈饥,使三千多户度过饥荒。吴师道任宁国路录事时,大旱,饥民载道。放赈粟、筹粮食,使三十余万人赖以存活。这是士人做官办慈善的主要工作。 二是士人作为官办慈善的推行者,认真担负守土牧民之责,根据当地实际,主动开展各类有效慈善。如果说,“落实”是做官办慈善的“规定动作”,有责任感的士则多做官办慈善推行的“自选动作”。唐朝郑损在关东出现瘟疫、死者如麻之时,主动督率年壮有力者进行义葬,每乡为一大墓,以葬弃尸。苏轼在密州,遇饥年,民多弃子,乃成立救婴组织,与刘彝等实施育婴惠政,“无疑为宋代慈善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0]5。苏轼在杭州中心修建了一所公立医院安乐坊,“就我所知,这个‘安乐坊’是中国最早的公立医院”[34]。明朝吕坤任济南道参政,建社学以助寒门,创冬生院以惠残疾。先后颁布《按察事宜》《存恤茕独》《收养孤老》等文告,提出了一些以顾恤残疾人为中心的独特的养济院政策。林则徐加强慈善组织建设,亲撰《敬节堂章程》,坚持慈善机构规范运作,大大提升慈善治理水平[35]。 三是士人作为官方慈善的创新者,面对社会问题,主动想方设法推出慈善新举措新方法,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这充分体现了士的慈善责任感、能动性。白居易在杭州任刺史时,主持兴修农田水利等工程,从贫苦人家中优先雇用。范仲淹知杭州,遇大旱,实施赈灾改革:以工代赈,大兴土木,增加就业;大办龙舟赛事,繁荣贸易,拉动内需;高价收粮,保持粮价稳定[36]。这些都为政府慈善开辟了新路。朱熹在崇安县逢荒年,向官府借米赈贷饥民,贷米于冬季归还,收息二分,若遇小饥,则利息减半,大灾全免。已注意借助市场手段。南宋真德秀任江东转运副使,创办建康慈幼庄,利用官田产业的租息佃钱收养遗弃幼婴。南宋黄震改革慈幼之政,提倡“保产”,即支发钱米给贫穷产妇,以避免弃婴溺女悲剧的发生。林则徐创设慈善机构的善款劝募及使用的整套办法,很早就注意到善款的保值、增值问题。类似案例举不胜举,这些改革举措冲破原有的慈善条条框框,甚至有的已经注意结合市场手段办慈善事业、有的接近现代公益的理念,很有慈善的创新意义。 在推动官办慈善的过程中,士人的积极作用通过其与统治者的互动得以实现,其中最重要的途径是谏言。“‘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传统的中国知识人认为诤谏是他们的天职。”[2]3与现代知识分子被称为“社会的良心”一样,“士”以直士之节,谏臣之舌,敢于向朝廷反映时弊、奉献对策。在慈善方面,“仁当养人义适宜,言可闻达力可施”[37]。“士”着眼大局,谏言献策,“为君解忧,为民请命”,以“一技一叶总关情”的心境,大胆反映“民间疾苦声”,推动官办慈善的发展。 “士”反映民情是多方法多途径的,最直接的手段是“上奏”“上书”,所谓“忧时七上皇帝书”,拼着老命反映亟待解决的民生问题,在中国古代慈善史上俯拾皆是。韩愈在做监察御史期间,京师地方春夏两季大旱,秋天又闹饥荒。京兆尹李实却贪财如命,不管百姓的死活,依旧对他们进行盘剥。韩愈于是写了一篇《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向皇帝如实报告情况。因此而获罪[38]。范仲淹任国子监时,江淮、京东遭灾。他看到灾民在吃一种带苦味的乌味草充饥,回京时带给仁宗,陈言“天之生物有时,而国家用之无度,天下安得不因”[36]2。 另外,对于民间苦状,士人还以擅长的诗画来反映,“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歌咏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39]。文学史上留下大量的民生诗、讽喻诗催人泪下。“‘放下筷子骂娘的白居易’写下了《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首。”[40]大众文艺出版社的《历代民生诗》、湖南教育出版社的《历代忧国忧民诗选》,收录大量士人的这类诗作名篇,他们写这类诗,“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41]。从唐宣宗李忱的《吊白居易》诗来看,“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42],“白居易们”的那些诗,皇帝有时是能够看到的。《中国救荒史》则记载:“我国历史上每次荒灾之后,流亡众多,农耕废弃,这种严重事实,历代关心民政的人,都有见到。忧时之士,并常以流民惨怛愁苦的生活,绘为图画以献于上。如:宋郑侠的《流民图》;明杨东明的《饥民图》;陈其猷的《流民图》及清蒋伊的《流民图》,都是很著名的。”[30]2 士人不单单只是简单地向统治者反映灾情,还充分运用其本身才识建言献策,面对灾情、民瘼提出解决方案,来影响高层决策,如苏轼所言,“为朝廷采摭四方利病”,让执政者“择其可行者行之”[43]。《中国救荒史》中用大量篇幅记录了这类对策,“赈济”“调粟”“养恤”“除害”“安辑”“蠲缓”“放贷”“节约”各方面,都有“忧时之士”献出良策。“各代著名学者和官吏的建议,都能够影响当时政府的实际政策,我们不可不加以注意。”[30] 3元初硕儒刘秉忠上书建议设孤老院,收养鳏寡孤独废疾者,供给衣粮,得到忽必烈采纳下诏。此后,元朝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对这些弱势群体的收养救助制度。清代士人陆曾禹作《救饥谱》,吏科给事中倪国琏为厘定进呈,乾隆命诸臣删润刊行,并赐名为《康济录》。《中国慈善简史》对此亦有大量记载,两宋曾巩、富弼、苏次、李钰等等建言献策,“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宋代慈善事业的繁荣与发展。”[10]5正如邓拓所说,“历代有较切实际的各种救荒议论。这些议论,多是由事实的逼迫而产生。它们产生以后,就往往成为实际政策的根据”[30]4,推动作用可谓大矣! 六、结语: 综上所述,在古代慈善事业发展上,“士”有很大、很高的慈善情怀。“士”在中国慈善史上发挥的作用是重要而全面的。在中国历史上,就慈善的承担者而言,有政府、宗族、个人等多个主体。其中,政府作为高举儒家治理思想旗帜的统治主体,为了落实其治理理念和实现长久、可持续的统治,天然地担负着慈善职责;宗族作为儒家血缘宗法制度的具体体现,对于血缘宗法共同体成员的关爱和帮助,也是血缘宗法共同体凝聚力的重要体现;另外,儒家哲学推崇对于他人的仁爱与恻隐,强调公共性优先于私人性,为善去恶,推已及人、兼善天下,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儒家这些重视社会的集体利益、重视他人的感受、重视自我约束的思想,也推动了历代儒者或者受到儒家思想影响的个人参与慈善活动中[44]。 纵观慈善历史,士人是政府慈善的主要执行者、落实者和重要推动者;是宗族慈善的主要组织者;是个人慈善的垂范者、倡导者。“中国有良心、有理性的知识分子总是站在广大人民的现实生活和长远幸福的立场。”[45]“士”除了传承儒家民本思想,还因为如马克思所说“有识之士往往通过无形的纽带同人民的肌体连在一起”[46],而担负起仁者爱人、济世救急的使命。 “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47]我们尽力挖掘士的慈善的事迹,充分肯定他们在古代慈善史上的地位、作用,就是要学习士的慈善传统的“典刑”(典型),让慈善美德时时闪耀,慈善传统大力弘扬,不断开拓现代公益慈善的美妙境界。 E N D
The Role of “Shi”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arity in Ancient China
YE Zhengmeng
(Yingxian Charity School,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China 310018)
Abstract: The “Shi”, as the guardians and promoters of spiritual values,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arity in ancient China. They enriched and developed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charity thoughts in ancient China, which guided their charitable practices. Charity in ancient China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folk charity and official charity. The “Shi” dominated the development of folk charity in ancient times, while also serving as the main body of local officials, effectively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official charity in ancient times.
Key words: Shi; Charity Thoughts; Folk Charity; Official Charity
(英文审校:黄璐)
参考文献:
[1] 参见:钱穆. 国史新论[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181。
[2] 参见:余英时. 士与中国文化[M]. 2 版.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2。
[3] 参见:赵剑敏. 〈中国古代士大夫的道义精神〉序[G]//汪元波. 中国古代士大夫的道义精神.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1。
[4] 参见:何立明. 中国士人[M].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1。
[5] 参见:周福岩. 民间故事的伦理思想研究:以耿村故事文本为对象[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45。
[6] 参见:习近平. 在中央党校建校 80 周年庆祝大会暨 2013 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13。
[7] 参见:王畿. 怀玉书院会语[G] / /郑秉文,施德容. 2020·慈善公益与脱贫.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45。
[8] 参见:李留德. 客商一览醒迷[G] // 郭梦钦. 经商语录.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8:59。
[9] 参见:张仲礼. 中国绅士的收入:《中国绅士》续篇[M]. 费成康,王寅通,译.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 社,2001:188-279。
[10] 参见:周秋光,曾桂林. 中国慈善简史[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1] 参见:许倬云. 我对伟大人物已不再有敬意与幻想[N]. 经济观察报,2020-12-30 :08。
[12] 参见:卢华语. 全唐诗:经济资料辑释与研究[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17。
[13] 参见:《新周刊》杂志社. 显微镜下的古人生活[M]. 长沙:岳麓书社,2020 :13。
[14] 参见:牟钟鉴. 儒道佛三教关系简明通史[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15] 参见:胡晓萍. 论道德圈的存在及其完善[J]. 社会科学研究,1997(1):9-11。
[16] 参见:朱健刚,武洹宇. 华人慈善:历史与文化[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2。
[17] 参见:史密斯. 中国人的性格[M]. 李明良,译.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046。
[18] 参见:包筠雅. 功过格:明清时期的社会变迁与道德秩序[M]. 杜正贞,张林,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19] 参见:范仲淹的“慈善信托”[N]. 学习时报. 2022-01-23(7)。
[20] 参见:资中筠. 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演变:美国百年公益发展的启示[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5:480。
[21] 参见:吕洪业. 中国古代慈善简史[M].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4。
[22] 参见:桓宽. 盐铁论[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39。
[23] 参见:吕不韦. 吕氏春秋[M]. 张双棣,张万彬,殷国光,等. 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6:158。
[24] 参见:马金章. 子贡与中华儒商文明[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
[25] 参见:叶正猛. 子贡:一个不应被忽视的古代慈善家[N]. 公益时报. 2022-10-11(16)。
[26] 参见:钱公辅. 义田记[G] // 吴楚材,吴调侯. 古文观止(下) 北京:中华书局,1959:422。
[27] 参见:宫蒲光. 关于走中国特色慈善之路的思考[J]. 社会保障评论,2022(1):117-132.
[28] 参见:王鸿. 中国特色的慈善传统[N]. 中华读书报,2015-07-08(10)。
[29] 参见:周秋光. 中国慈善史研究再出发[J]. 安徽史学,2020(2):5-9
[30] 参见:邓拓. 中国救荒史[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
[31] 参见:汪元波. 中国古代士大夫的道义精神[M].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47。
[32] 参见:周易[M]. 杨天才,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6:18。
[33] 参见:陈志武. 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的博弈(上)[M]. 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2:134。
[34] 参见:林语堂. 苏东坡传[M]. 宋碧云,译. 台北:台北市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1:264。
[35] 参见:李春伟. 林则徐的公益事业管理观[N]. 公益时报,2017-03-30(12)。
[36] 参见:范矛彧. 伟大的慈善家范仲淹[G]//刘道兴,杨德堂. 范仲淹文化研究.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
[37] 参见:欧阳修. 食糟民[G]//周溯源. 历代忧国忧民诗选.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164。
[38] 参见:中华书局《月读》编辑部. 文人为官[M]. 北京:大有书局,2021:137。
[39] 参见:白居易. 与元九书[G]//郭绍虞,王文生. 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96。
[40] 参见;王晓磊. 六神磊磊读唐诗[M].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270 。
[41] 参见:白居易. 寄唐生[G] // 顾学颉,周汝昌. 白居易诗选.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52。
[42] 参见:李忱. 吊白居易[G] // 彭定求. 全唐诗(第一册). 北京:中华书局,1960:49。
[43] 参见:吴桂就. 苏轼的政治主张及其民生观[J]. 古典文学论丛,1980(1):235-256。
[44] 参见:朱承、刘佳. 儒家“扶危济困”的思想与实践[G] // 郑秉文,施德容. 2020·慈善公益与脱贫.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60。
[45] 参见:郑文龙. 杜维明学术文化随笔[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317。
[46]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78。
[47] 参见:文天祥. 正气歌[G] // 朱东润. 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第二册中编).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