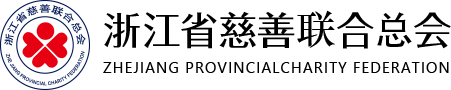“劝善”是中华民族悠久的传统。《汉书·公孙弘传》曰:“臣闻上古尧、舜之时,不贵爵赏而民劝善。”——即是说上古尧舜那个时期,不重于官爵行赏,但百姓却相互勉励为善。笔者提出,史上劝善有“三大奇观”:百姓万家的“家训”、千村万落的“乡约”、卷帙浩繁的“善书”。笔者作文品评“三大奇观”,已经发表《慈善是优良家风传承永恒的脉动》《传统乡约的慈善表达及其当代意蕴》两篇,今作第三篇《古代善书曾长期风行的一个奥秘》。
善书,又称劝善书,是劝导人们行善止恶的指导书。吴震说:“所谓‘善书’究其思想之实质而言,其宗旨无非就是以道德立说,劝人为善。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善书运动’其实也就是‘劝善运动’。”(吴震《明末清初善书运动思想研究》)
当代人知道的第一本善书大概率是《太上感应篇》,是从茅盾小说《子夜》或同名电影电视剧得知。《子夜》开篇“吴老太爷进城”,叙述吴老太爷为逃避“匪乱”,坐船来到上海,在大都市霓虹灯闪烁中,捧起了《太上感应篇》。最后,忍受不了种种强烈刺激,脑充血而亡。小说写道:“坐在这样近代交通的利器上,驱驰于三百万人口的东方大都市上海的大街,而却捧了《太上感应篇》,心里专念着文昌帝君的‘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的诰诫,这矛盾是很显然的了。”文学评论一直将吴老太爷作为愚顽不化的“古老的封建僵尸”形象(作者也留下一个一般评论家不解之谜——“可是三十年前,吴老太爷却还是顶括括的‘维新党’。”)
品评善书,先从《吴老太爷进城》这个桥段说起,首先是想说明,古代善书和劝善运动不可避免地掺杂有不少封建意识和落后愚昧的观念,对它并不可一味地唱赞歌。本文试图对它作为中国伦理史上一个独特的、而今天已经比较陌生的现象,作一个客观的介绍、分析,主要探寻其曾长期风行、长盛不衰的内在原因,从中得到对当代慈善宣传教育的有益启示。
劝善书源自于秦汉,兴起于宋代,盛行于明清,延续至民国。古代善书可谓卷帙浩繁、汗牛充栋。有学者推测在十万种以上。台湾一公司建立了“中国善书大全数据库”,收集在台湾出版的善书4万余种。2018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劝善书汇编》共201卷。
“向上向善的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休戚与共、血脉相连的重要纽带。”《周易》曰:“君子以教思无穷。”孔子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善书确实发挥过积极作用。其意义归结到一点就是“善与人同”。“善与人同”一词,始见于《孟子·公孙丑上》。偕同别人一齐行善,是君子最高的德行。“善书使人读后易起善心、力行善事,把行善的风气推而广之。因此,善书编刊者称‘同善之士’……。个人力量有限,其善行期望‘广其善端’‘广结善缘’,进而更多人‘共襄善举’。”(游子安《善与人同——明清以来的慈善与教化》)
善书影响非常大。从时间上说,影响了宋代以降的中国社会;从空间上说,波及到亚洲儒家文化圈。
——刘子健说:“最能代表中国多数人信仰的不是《论语》、不是《传灯录》、不是《近思录》、不是《道德经》,而是这些大批各种的善书。”(刘子健《明代在文化史上的估计》)
——杨联升说,宋代的《太上感应篇》,是最受推崇的一部,据20世纪早期所做的一项估计,《太上感应篇》的版本可能较《圣经》或莎士比亚著作的版本更多(杨联升《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之意义》)。
——日本酒井忠夫的《中国善书研究》说:“‘善书’传播到亚洲各国,影响了各国的民众文化,特别是对江户时代的日本文化影响甚大。”
——游子安《劝善金箴》一书说:“饶有意义的是,善书经过近代政治、社会、文化的变动,快要踏入21世纪之际,善书仍不失其劝善的功能。时到今日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善人与佛道团体,还是继替不绝的撰著、纂编、注解及印送善书,‘善书传统’一直风靡不衰。”
品评善书,笔者十分着意善书中的“慈善”。其一,善书之“善”、劝善之“善”当然不全是慈善,但慈善是其重要内容。其二,“中国传统慈善事业极为重视劝善功能,劝人为善历来是慈善事业的题中应有之义。”(王卫平《救济与劝善:“慈善”本义的历史考察》) 古人说:“作善无穷,此愿先从刊布善书起。”
抚今追昔,善书和劝善运动曾长期风行,对中国社会产生深刻影响,其原因何在呢?综合起来分析,除了特定的历史社会环境之外,善书和劝善运动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借用《周易》的话来说:“同归而殊涂(途),一致而百虑。”(共同的归宿而所走的道路不一样,达到同一个目的而想法有多种。)就是“道虽一致,涂(途)有万端。”(陆机《秋胡行》)善书和劝善运动,以“善”为归宿,在内容、形式、方法、途径上都体现了多样化,以适应不同人群、不同层次伦理道德建设的实际。可视为古代善书曾长期风行的一个奥秘。这是善书和劝善运动最值得我们探究和借鉴的地方。
一、“一二三多”:劝善文化的整体性与组合要素的多元性。
从中国社会传统和思想源流上看,“善是中国人之‘魂’,是社会人生的依靠和凭借。”(游子安)善,植根深厚,成为中华文化的圭臬、民族的瑰宝。善书和劝善运动“善”的理念构筑了劝善文化的整体性。梁漱溟说:“宗教、道德二者,对个人都是要人向上迁善。”如南宋著名理学家陆九渊所说:“东圣西圣,心同理同。”同时,善书“善”的理念源出于不同宗教、不同伦理道德学派,其组合要素又体现了多元性。
中国传统文化是“多元一体”的结构。牟钟鉴说,两千年中华思想文化在动态中形成的结构,可用“一二三多”来概括。“一”是儒家主导,“二”是儒道互补,“三”是儒道佛合流,“多”是包纳其他宗教和外来文化(牟钟鉴《儒道佛三教关系简明通史》)。这个结构模式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与开放性的有机统一。“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来无所谓宗教的概念,儒、释、道皆可以教化众生,皆可以为宗教。”(王守常《中国智慧》)从慈善文化来说,儒家主张仁者爱人,德化人生;道家主张积德、济世,劝善、承负;佛家主张慈悲为怀,慈航普渡;还有墨家主张兼爱;外来基督教主张“博爱”“爱人如己”。
善书最能体现“多元一体”文化结构,其内容充分反映出:“三教虽殊,劝善义一,涂(途)迹诚异,理会则同。”(北朝释道安《二教论》)
研究善书的学者一般认为支配中国国民精神的儒佛道三教中,最有势力的是道教。道教的善书,出现时间较早,影响较大,数量较多。《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关圣帝君觉世真经》三种被称为“三圣经”,在民间有经典的地位。
晚明之后“化儒学为宗教”的思想动向十分明显。明末善书主要是“现世化”与“儒家化”的善书,如袁黄的《阴骘录》、颜茂猷《迪吉录》等。
在佛教中国化进程中,出现了以“劝善”为题材的佛教劝善典籍。此类佛门劝善典籍既以“疑伪经”的形式出现,又以“释氏辅教书”之类的志怪小说、佛经应验记及变文俗讲等形式出现;还有佛门“功过格”“宝卷”。
“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善书更多体现了三教融合。其代表作是袁了凡的《了凡四训》。该书“糅合了儒、道、佛三家的思想学说,阐明忠孝仁义、诸善奉行以及立身处世之学。基本统摄了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中华书局《<了凡四训>前言》)现存善书大多数也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融合的倾向。
体现劝善文化“一二三多”之“多”,还有少数民族的善书。以云南大理为例,这是汉族和白族、彝族、回族等多民族聚居地。清末、民国年间善书大量流行。善书既体现对中华民族大家庭共同文化的价值认知,也蕴含少数民族自身的文化特色。
耐人寻味的是,清末、民国时期外国的一些传教士,也以“劝善”的姿态介入中国民间社会。他们“蹭”中国善书名头,以“劝世良言”之类为书名,传扬《圣经》内容。
真可谓是“众芳争妍,各呈异彩。”
劝善文化组合要素的多元性可以达到更大的劝善实际效果。其一,各门各派“不约而同”开展劝善行动,推广各自善书,适合了不同文化层次、不同宗教信仰的群众;其二,善书出现三教融合态势,“这种合一、混一的主张,……也解放了接受某种主张的信仰者的头脑,扩大了某种学派成员的选择空间。”(王蒙、赵士林《争鸣传统》)
二、“同归殊途”:劝善目标的一致性与方法途径的多样性。
善书和劝善运动的目标是明确的、一致的,就是善与人同、人人为善。而细究善书群书、纵观劝善运动过程,其内容、形式、方法、途径等等,都呈现出多样性;由多样性而更多地指向简易性、通俗性;由此客观上提高劝善的实效性和持续性。
第一,为善动因“假设”的多样性。
劝人为善,首先要作好对象为善的动因“假设”,即站在对象的角度考量“人为什么为善行善?”道德建设很大程度上反应在道德自律与他律之上。各类善书作出了多种假设,在此基础上“有的放矢”进行劝谕,以适应不同层次、不同群体的道德水平。
其一,道德自律、道德内省,唤起人们道德自觉。“在中华文明之中,道德的自律至关重要。为什么欧洲启蒙思想家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呢?因为中国文化可以充分调动人的自觉性,道德的自觉和自律就是维系中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的根本基点。”(王守常)对此,善书是一个很好的体现。例如,明代士君子刘宗周著名的善书《人谱》,相信心为至善,倡导挖掘自身道德潜力、保持“慎独”即初心的纯洁;并且设计了“诚意之教”的具有可操作性的修养方式。还有不少善书都属于这一类善书。
其二,道德他律,把上天、鬼神、佛陀……作为道德监督者。“人间私语,天闻若雷;暗室欺心,神目如电。”善书的思想融入了儒家的“留余庆”观念、佛家的因果轮回观念及道教的积善销恶承负观,结合民间伦理观念,使“因果报应”成了善书和劝善运动的一个重要基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行。”(《太上感应篇》)
对善书大量呈现的“因果报应”内容,现代人可以作出种种不同的评价。但是,它比较符合当时民间伦理观念,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果报应是人民支配日常行为的生活规范与价值标准 ”(郑志明《中国善书与宗教》)对传统民间道德建设起到一定的正向作用。
《了凡四训》提出“命由我作,福自己求”的命题,则力图将自律和他律加以揉合,指出只要积善累德、谦恭卑下、感格上天,就能够求福得福,安乐无尽。书中引用六祖禅师箴言:“一切福田,不离方寸。从心而觅,感无不通。”
另外,善书强化“报恩”思想,促动人们行善。
行善动因“假设”,《文昌帝君蕉窗圣训》道出了真谛:“遇上等人说性理,遇中等人说因果。”为善动因“假设”的多样性,是为了提高劝善的针对性。
第二,劝善对象的多样性。
善书劝善,目的是相同的。因而,善书有普劝善书,宣扬普遍适用的善念,如劝善书的经典之作《太上感应篇》。同时,善书流行的一大特点是,针对不同层次的人群,包括阶层、职业、性别、年龄、贫富等不同,编撰不同的教化善书,或者在同一善书对不同人群提出不同要求、期望,因而,“显现社会分层劝戒的特色”。(游子安《劝化金箴——清代劝善书研究》)
第三,劝善“主角”的多样性。
善书的作者有儒、道、佛诸家学者,有民间知识分子,还有政府官员;不少皇帝也亲颁善书,著名的有朱元璋的《六谕》,康熙的《圣谕十六条》、雍正的《圣谕广训》等,风行一时。善书主角多样化必然体现道德要求的层次化。
第四,劝善方法的多样性。
一是体裁、形式多样。善书种类繁多,形式不拘一格,除了劝善文基本形式的之外,面向普通民众还有多种多样的体裁。劝善文分为说理为主和纪事为主两类。说理类善书流传很多;纪事类如宋代的《劝善录》、明代的《迪吉录》。纪事性劝善故事如“范文正公义田记”“裴度还带”“两宋渡蚁”等类似现在的微型小说广泛流传。还有一种是说理与记事相结合的劝善文,如上述《了凡四训》。
与劝善文具有同等分量是“量化善书”,就是将各类善、恶表现进行分门别类,使用者据此进行善、恶量化计算,以求扬善去恶、日日有进。儒、道、佛的种种“功过格”“功德例”均属此类。
图说善书,是用易于理解的浅显图画来宣传为善、行善,有的再配以简单文字说明,如《圣谕像解》《太上感应篇图说》。
大量诗歌形式的善书称为劝善歌,如《劝世诗歌》。以格言、箴铭劝善是又一大特色,且影响特别广泛、深远,如《忍字箴》《醒世恒言》等等 。还有为善警句散见于善书之中,如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太上感应篇》)。“欲广福田,须凭心地。”(《文昌阴骘文》)“善恶两途,祸福攸分;行善福报,作恶祸临。”(《关帝觉世经》)……,这些警句名言,一直流传、影响到今天。
二是传播方式多样。劝善还通过宣讲、说唱等方式来宣传劝善书所蕴涵的道理。善书“宝卷”是一种在宗教和民间信仰活动中,按照一定的仪轨演唱的说唱文学体裁。还有采用了戏曲、民间小调等文艺形式宣传。
明代出现地方性的讲会组织,如颜茂猷的云起社,目的是改变地方风俗,由“一乡之善”而“远至一国,远至天下”。清代还出现了由乡绅、士人及工商富裕阶层组成的民间宣讲共同体,进一步推动慈善教化的民间化。
煞费心思,力求形式多样化,其目的为了“务使人人易晓,感动善心。”(陈龙正《同善会会式》)
第五,善行实践途径的多样性。
善书和劝善运动着眼道德实践。王卫平指出:“行善与劝善并重,致力于教养兼施,物质帮助与移风易俗、改造社会两不偏废。”(王卫平)在此基础上,善书体现道德修养和行善途径的多样化,以有利于人们的道德实践。
从慈善的角度分析,善书的主张如同先秦墨子所说:“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善书表述了慈善的多种方式途径,供不同人群选择施行。值得注意的当时有一种善书,叫“不费钱功德例”,就是经济条件不好的一般群众,也可以选择做慈善、行“功德”。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愿意行善者众,出钱行善者难,这种劝善安排可以鼓励更多人参与慈善。
王元化提出事物发展有矛盾、有差异,因而他提出的命题是:“多样性的统一”(王元化《思辨录》)。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说:“俗话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看情形办理,文章和演说也是这样。”多样化,能扩大选择面;多样化,能产生适应性;多样化,能增强融合度;多样化,能提高实效率。劝善运动的这一重要经验,对今天慈善公益宣传教育和劝善劝捐仍具有启示意义。
三、“理一分殊”:终极善念的归一性与道德要求的层次性。
理一分殊,是中国伦理学史上一个重要命题,恰可用来作为善书和劝善运动的“同归殊途”特色的理论诠释。
什么叫“理一分殊”?朱熹说:“合而言之,则莫非此理,然其中无一物不该,便自有许差别,虽散殊错糅,不可名状,而纤微之间,同异毕显,所谓理一而分殊也。”(《延平答问》)
在此且不细论“理一分殊”作为朱熹天理观的重要内容的深层意蕴。——其说“理一”,是“理”寓于“气”及万事万物之中;其说“分殊”,是因为“同者理也,不同者气也。”(《语类》卷一)——上升到哲学层面,有些玄奥。沈善洪、王凤贤的《中国伦理思想史》中有一个通俗的解释:“‘理一分殊’是朱熹用以回答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关系,尤其是解决统一的封建道德与处在不同阶级、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所担当的不同的道德责任的关系的一个重要命题。”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认为,道德的层次性特征是客观存在的。一定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下的道德教育、道德引导,应该区分与适应不同层次的道德水平。注重一般性道德规范,提倡追求高层次引领,着力激励低层次提升,以促进全社会道德的分层升格。因而,任何社会都存在一元导向和多层取向的价值关系。“理一分殊”理论的可贵之处在于,它说明处于封建社会中的教化也不应是“铁板一块”的。
宋代以降,善书和劝善运动终极善念的归一性与道德要求的层次性相统一,很大程度上受到“理一分殊”理论的影响。因而,善书和劝善运动注重了“大传统”与“小传统”相融合。笔者三篇“品评”文章都提及这个融合,这应该是慈善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国外历史研究一个“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分类方法。亦即历史上存在一个“精英思想史”和与之相对应、包括民间的思想、民众的思想在内的“一般思想史”。中国民俗学分为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中共二十大报告有新的精辟论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我们研探传统慈善文化,不仅要研究“主流”的思想、经典的论述,也要探索民间的价值观念。把精英思想引入民间,并同民间共同价值观相结合,由此体现出“同归殊途”“多样性的统一”的特色,这是善书和劝善运动、也是“三大奇观”留给我们最值得借鉴的经验之一。
王卫平曾强调说:“现代中国慈善事业的复兴及其具体理念受到西方文化的一些影响,而中国历史上的某些慈善传统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人往往将慈善事业简单地视为捐款捐物,仅仅限于对社会弱势人群予以物质帮助,而其中应有的道德教化、劝人为善等功能未能得到很好的传承与弘扬。”史上劝善“三大奇观”,有许多方面经验值得我们深入挖掘并借鉴。